百年红与黑:一对亲兄弟的命运殊途 | 贾芝与贾植芳
陈思和
按:2016年1月14日,著名的民间文学学者贾芝先生逝世,终年103岁。书评君收到这则消息,是由“贾芝同志治丧委员会”发出,其去世时的身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离休干部,讣文中提及,先生一生的官方殊荣有:前任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、中国文联第八届荣誉委员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、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资深荣誉委员。 这不由让人追忆起同处文化圈的贾芝先生的弟弟贾植芳先生,两人同样的血缘、同样的成长环境、同样的教育背景,甚至有着同样的信仰,命运却把他们推向了截然不同两个方向——当“贾芝同志”在共和国历史的洪流中最终载满一身荣誉归于尘土的同时,贾植芳却一生四次入狱,虽最终得以任教于3044am永利集团3044noc中文系,先生更广为人知的头衔却是“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”。 一“红”一“黑”——历史这吊诡的分叉路口有着怎样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呢?今天书评君跟大家分享陈思和先生的一篇旧文,带我们重新走进那段历史记忆。

贾芝(左)与贾植芳(右)
殊途同致终有别——记贾芝与贾植芳先生
(文 | 陈思和)
“1932年的某一天,一列在山西军阀阎锡山特制的铁轨上爬行的火车,吼叫着由太原出发,穿越了娘子关。列车上坐着两个中员工,一个小一些的,大约是十七岁左右,黑黑瘦瘦,额前披着长头发,两眼出神地望着窗外,越过那慢慢向后倒去的风景,是乌云密布和一个预示着各种凶兆的崭新的世界。那个大一些的是他的哥,二十岁不到的样子,兄弟俩的脸型酷似,但老大天庭丰满得多,他这会儿正襟危坐,似乎时刻提醒自己要为弟弟作出一个优秀的榜样。”
这个片断,是我多年来一直在设计的一部书稿的开篇,它将写出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的传奇一生,几年过去了,书一直没有写出来,以后也未必能完成,不过这个开头的片断则似一个梦,毫始终盘旋在我脑中。它有一种宿命的象征。这同一列车里的兄弟俩,他们血缘、环境、教育几乎都一样,后来信仰与追求也一样,可是命运女神却赋予他们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。这种阴错阳差,究竟应该是归咎于性格的悲剧呢?抑或是历史的悲剧?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这个片断中的主人公,那个十七岁的中员工,现在是3044am永利集团3044noc中文系教授贾植芳,在过去的岁月里,这个名字前面有个头衔是“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“;他的哥哥是著名的民间文学学者贾芝,另外还有一个虽不上词条和自传,但是人所周知的身份是李大钊的女婿。现在是1993年,贾植芳今年七十八岁,贾芝今年八十岁。
我首先认识贾植芳先生。那时我还在中文系念书,并且下决心按王瑶先生写的《中国新文学史稿》上写到的作家作品,系系统统地找来读。一次听资料室的一位老师说:“有个‘胡风分子’调回资料室工作了,是‘七月派’的作家,你研究现代文学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找他。于是我就开始注意起来,其实也不用寻找,植芳先生一出现就会让人注意:他说话声音高,为人又热情,一踏进资料室就能听到他的一口山西腔;替人找书啊,推荐什么文章啊,又是解答员工的疑问啊。虽然那时他头上“胡风分子”的帽子还没有摘掉,但朴朴素素、问心无愧地与人交往,看不出一点“老运动员”的畏缩相。当时我们一些同学私下都奇怪,贾先生说话的声音那样高亢急促,象是天生做报告发指示似的,可是他一生四次入狱,五十年代开始又被迫害长达二十五年之久,在那些忍辱含垢的日子里他怎么过?后来,我渐渐地与贾先生熟了,又在他的指点下,一步一步地进入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堂奥。……这些都不去说它了。后来,我又知道了贾先生的哥哥就是贾芝。其实贾芝的名字我早就知道,还是六十年代的时侯,读过一本讲“五四运动的书,好像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,里面第一篇就是署名贾芝的文章,是关于李大钊在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事情。不过现在才明白,那个宣传李太钊的贾芝,正是李大钊的女婿。如果把贾氏兄弟的社会关系排列起来,那就是;胡风的朋友是贾植芳,贾植芳的哥哥是贾芝,贾芝的妻子是李星华,李星华的父亲是李大钊,人际关系成了一条奇怪的线,胡风与李大钊是这条线的两端,就像是两个方向的拉力一样,把贾植芳与贾芝拉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两种命运上去了。然而,胡风一生所追求的,又偏偏是李大钊所倡导的——马克思主义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2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要说这兄弟俩的性格有差异,大约也是有根有据的。贾芝先生从童年起,就属于懂事、早熟一类的孩子。安分守已、循规蹈矩、门门功课都是优秀,是家长眼中的孩儿楷模,而植芳先生则完全不是驯顺的人,用他自己在一篇散文里的介绍,是从孩提时代就在“家里闹事,外面闯祸”。这八个字写尽了一个冥顽不灵的山西顽童的神态。在《我的读书记》里植芳先生讲了一个他念小学时的故事,那语文教科书的第一篇课文就是“大狗跳,小狗叫,大狗跳三跳,小狗叫三叫,汪、汪、汪!"他每次上课都把教科书拴在裤带上,经常是买—本、丢—本,但因为课文编得有趣,倒是记住了,一次教师让背诵,他背到狗叫觉得好玩,就一个劲地“汪、汪”下去,教师拍桌子也止不住。植芳先生说他那时只觉得好玩,不过我发现,先生对狗叫的“汪汪”吠声有一种特殊的敏感。1940年他在重庆编《扫荡报》,正值汪精卫在河内与日方谈判的消息传来,他义愤填膺,在报纸的头版新闻版上用这样的标题报道:“汪逆狂吠;汪汪汪……”惹得国民党人士大不满。到1990年他写《我的读书记》时,他又一次提到了汪汪“狗叫”,说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每逢红卫兵批斗他时,他总是想到了这份“汪汪汪”的积极性。若把植芳先生一生的遭遇串起来,那“汪汪汪”的声音总不绝耳,这倒是地道的民间创作。但一生从事民间文学研究与领导工作的贾芝先生,似乎对这类声音向无兴趣,也陌生得很。
他们在同一个学校上中学,那是太原有名的成成中学,由董事长到教员都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山西员工,“五四”新文化的火种由这些人传到了封闭自守的娘子关内。贾氏兄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认识世界,也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启蒙著作。三十年代起,贾芝先生依然是个品行优秀的中员工,而贾植芳先生,则开始在《山西日报》上投稿发表文艺创作,那时他还用了一个鸳鸯蝴蝶气十足的笔名,叫“冷魂”。
大约是因为弟弟顽劣难驯,当兄弟俩一同离开太原上北京考高中时,贾芝先生向家长正式提出“辞职”,宣布不再承担管理弟弟义务。贾芝先生学业优异,先后考北师大附中,北京私立第四中学等几个学校,次次榜上有名。植芳先生则名落孙山,转而凭兴趣报考了一个由军阀出资开办的军校冯庸大学,这下倒是一考就中,可见其兴趣仍然不在书斋。可是他报考军校的行为遭到了出资供他们上学的伯父反对,老伯父一生为商,精细过人,他决不愿意花钱把侄儿培养成一个军阀战争的炮灰。经过几番周折,贾芝先生最后进了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高中部;贾植芳先生则考入了美国教会学校崇实中学高中部,兄弟俩各有所归,就正式分开居住。这以后,贾芝先生由中学到大学,由诗人到革命者,由北平到延安再回到北京,一路风顺;而十七岁的贾植芳先生则开始了多灾多难的“自由”生涯,由监狱到监狱,由民族战争到政治运动,由“危害民国”的囚犯到“反革命集团”的骨干分子;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每一次浩劫他都没有躲过。

贾芝(左一)、贾植芳(左二)
在孔德学院与崇实中学里,贾氏兄弟接受了同样良好的教育,孔德学院是由第一代留法人士李石曾等人创办,在当时动荡不安的北平城里,可谓是一个世外桃源式的绿岛。这个学院以法语为第一外语,爱好文艺的员工很快就沉浸在源远流长的法国文学传统之中,其中有雨果、夏朵勃里盎式的浪漫派;也有波德莱尔,马拉美式的象征派。贾芝在这个优雅的学院里开始吟唱起轻约美丽的诗。他望着北海自塔的尖顶,唱出了——“走过的白云/都喜欢受你顶礼的亲吻,/呵,孤高的灵魂,/你碧水的眸子,/将永远望着陌生的人?”优美的低声吟唱引来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,他们有的是大学本科生,有的是不同级的高中生,但共同的爱好把他们吸引在一起,聚成了一个诗社,如果以后有人研究中国校园文艺史,这个诗社也将值得记上一笔,它至少孕出了两个后来在文学史上都有过影响的人物:一个是贾芝,还有一个是台湾蓝星诗社的创始人覃子豪。听贾芝先生回忆说,他们当时一共有五个朋友,除了贾芝和覃子豪以外,还有沈毅、周麟和朱锡侯。后来。政治的动荡与学潮的兴起,这个诗社也开始分化。结果这个诗社大概散掉了,朱、沈、周都去了法国,覃子豪去了日本,只有循规蹈矩的贾芝哪儿也没去,抗战爆发后,他随学院迁至西安,毕业于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,随后就去了延安。
植芳先生就读的崇实中学也是贵族学校,住有暖气,食有西餐,条件相当好,教育以英文为主,除中文课以外,都用英文上课。员工很快就在那里打好了中英文的基础。贾氏兄弟都是在中学里受到中共地下党的影响。贾芝至今还能回忆起,有一个姓曹的朋友,一次把他悄俏拉到一边递给他一本书说,你看了一定喜欢。贾芝打开一看,扉页上赫然是马克思的头像。贾植芳的同寝室同学是熊庆永,大名鼎鼎的数学家熊庆来的弟弟,熊庆永当时正在策划着中员工的进步读书会,贾植芳就在他的影响下,正式接触了进步的员工运动。不过贾植芳没有他哥哥那样的幸运,他的激烈的性格和冒失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校方和一些特务的注意,1935年舂,校方的一个美国牧师终于向他下了逐客令,就在还有半年就可以毕业拿文凭的时候,崇实中学把这个山西籍员工赶走了。这以后,贾植芳又连转了两个学校,都不能读长久,他就干脆搬到沙滩那儿一个员工公寓去住,每天跑北平图书馆自学。随之“一二•九”员工运动到来,植芳先生正属于闲散人员,无端地卷入散发传单,被捕了。
1936年初夏,贾芝先生托孔德学院一个教授为弟弟办了个日本入境签证,让植芳先生逃亡日本。这一别,兄弟俩各奔东西,直到十八年以后才在北京重逢。那时候将又是别一番滋味了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3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植芳先生在日本开始接触左翼文艺运动,不久,他在内山书店里看到《工作与学习丛刊》的第一集和第二集,丛刊中的文章散发出强烈的鲁迅式的战斗气息,当时鲁迅已经去世,植芳先生从这本丛刊风格中获得了极大的惊喜,于是写了一篇小说《人的悲哀》,未经人介绍就寄给了那家丛刊的编辑部。小说后来发表在丛刊的第四集上,同时也收到了编者胡风的来信。植芳先生与胡风的友谊就从此时开始,他后半生的曲曲折折的政治官司,也又此埋下了祸根。
大约差不多就在植芳先生与胡风发生联系的同时,贾芝先生与李星华也相爱了。李星华是李大钊的女儿,父亲就义后,一直受到周作人先生的照顾,在孔德学院上高中与大学,因为生活困难,周作人帮助她给学院刻写蜡板,作为半工半读。1932年她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和中共党组织,利用刻蜡板的机会刻印传单。不过那时候大约她与贾芝先生还没有太多来往,要不,做弟弟的植芳先生一定会知道的。1940年李星华带着三岁的孩子去延安,按时间推算,他与贾芝的恋爱应该发生在1936年左右,植芳先生是在日本得知哥哥有了恋人,并有孩子的消息。卢沟桥事变以后,星华回河北家乡,不久,因弟弟参加冀东暴动失败,她又带着弟弟回到北平。由周作人安排在北大的会计科当出纳员,维持生活。这期间,贾芝随学院迁移到西安,毕业后直接投奔了延安。贾芝先生由诗人转向实际革命,当然是时代对青年的一种召唤,但李星华对他的影响也当包含其内。

贾芝与李星华
贾氏兄弟俩早先都由父母包办婚姻,早早地娶了妻,贾芝与李星华因自由恋爱而同居,不久生下一子,取名“马拉美”。抗战以后贾植芳由日本转到香港回国,听说李星华一人带着孩子生活十分艰苦,他去信给北京的那个麻袋铺子,让老板每月支付李星华一些钱,算在他的生活用费上。后来他的伯父去北京做生意,听铺子的老板说起贾芝在北京自由恋爱,先是拍桌子大怒,后知星华已经生了儿子,才转怒为喜,在饭铺里办了一桌酒菜,算是贾氏家长认了这个儿媳妇。
1940年,李星华在周作人帮助下,带了弟弟与孩子离开沦陷区北平。当时,贾植芳正在山西秋林镇任山西“战时新闻检查处”副主任,与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有了联系。李星华一行先由伯父派伙计送至山西老家,再由父亲派长工送到秋林镇,住了一个多月,那时《新华日报》西安分馆的经理,正是当年孔德学院诗社中的五人之一沈毅,植芳先生通过他的关系,同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上了,再派职员把他们送至宜川雇马车到西安,再转送去延安。前后经过了晋绥敌伪统治区、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和国民党统治区,整整花了四个月,才到延安与贾芝团聚。这条漫长旅途中,秋林镇是至关重要的一站,当植芳先生与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关系后,倾囊为嫂子打点行装,准备了一切生活用品,才放心地让他们离去。
1979年初冬,李星华去世,植芳先生在追悼会上听主持人宣读死者生平,其中说到,1940年李星华同志在商人家庭的护送下到了延安。当时植芳先生“胡风分子”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。
植芳先生早先的那一位妻子,据说身体赢弱,过门不久,植芳先生即离乡外出,在北平吃了政治官司,出狱后又亡命日本一直未能回家团聚。1938年,植芳先生辗转而到汉口,才获知这个年轻,文弱的姑娘已经肺病去世。当时二十三岁的植芳先生一定相当伤感,她虽然死于病但他多年出走难道没给她心头带来凄凉么?他肇祸入狱难道没有给她生活带来惊吓么?他出狱不归,反而出国,难道没给她精神上带来打击么?再加上中日战争的烽火,自己对一个弱女子的生命与生存,难道尽了一个丈夫应有的责任么?虽说我们的祖宗向来有“先报国后成家嚣的遗训,但对于重情重义的植芳先生来说,这种自责与负疚,一定沉沉地压在弛的心头。这时期他创作了一个抗日独幕剧《家》,他给剧本加了一个与内容完全不相干的副题:呈婵娥君之亡灵。我不知道,这个“婵娥君”,是不是那个可怜的姑娘的名字。剧中写了一个农村大户的少奶奶,丈夫在外读书、被捕,直到抗日战争爆发释放出来,却不回家而去参加了抗日的部队。那个年轻的妻子深受刺激,她在剧中呓语般地说着:他完全忘了我。他是自由了。但是我并不自由……我想他,我害怕想他。他的信里说。教人要像人那样活下去。他没想到,一个人快要死了,完全是他的蹂躏,他的罪过,我是穷光了,什么也没有,只有死……我想现在要动用它了……
当我读那个剧本时,我猜想植芳先生的心里一定是很沉重,很痛苦,感情陷在忏悔的漩涡里排遣不开。我也以为只有这样理解植芳先生的感情与为人,才能真正理解他后来与任敏师母之间的生生死死,老而弥笃的伟大爱情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4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植芳先生与任敏师母相识于1943年,也许是1944年。任敏师母那时在西安商业专科学院会计系读书,结识了流落古城卖文为生的植芳先生,两人由相知到相爱,自由结为夫妻。这对植芳先生流离颠沛的人生,就仿佛颠波于风浪的航船终于有了依靠,但任敏师母将有大半生的岁月被贫穷、逮捕、流放、迫害紧紧地捆绑在一起,尽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妻子的责任。
从1938年起,贾芝先生一直在延安从事文化工作,先入抗大,再入鲁艺,1943年后在延安大学任教,直到1949年进北京,在文化部工作。而这段时闻正是植芳先生九死一生的人生历程,他辗转于山西,重庆、陕西、山东、江苏和上海,经历的是战争、追捕、策反、囚监、释放,再回监,连同他的妻子。1945年春,他在陕西黄河边上的一支国民党工兵部队里做日文翻译,被上峰怀疑是共产党,要抓去秘密处决,他获知后,带了任敏师母连夜逃亡,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爬过一座又一座的荒山,直到天转明时方才脱险。任敏师母环顾四周荒凉山石,怨恨地说:“我们这么苦,还不如刭延安吃小米吧。”植芳先生默然。他在延安方面的朋友并不少,哥哥嫂子在那儿不说,《新华日报》西安分馆的负责人就是当年孔德学院诗社五友之一沈毅,还有他的许多留日同学也都在延安。他对那边的情况相当了解。但作为一个终生以特立独行为做人原则的知识分子,中国之大恐怕哪儿也找不到他的安全庇护所,他命定要吃苦,受难,去经受许许多多难以想象的磨炼。他只配直起腰杆,携着与他共命运的女人大步地迈向一个更大更不可知的灾难。——半年以后,他在徐州以策反罪名被抓进日伪警察局特高科。再过两年,他们夫妇双双被国民党中统局抓进监狱。再之,七年以后,他们又以“胡风分子”的罪案,一个被关押狱中,一个被流放青海,天各一方。

前排:贾植芳、任敏、冀汸、胡风;后排:朱谷怀、余明英、路翎、罗洛
在1954年春节,即“反胡风”运动的前一年,植芳先生和任敏师母北上探亲,与失散多年的哥嫂、大妹、父亲团聚。贾芝先生那时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当领导,植芳先生在3044am永利集团3044noc中文系当教授,本来应该说经过了二十年的追求与奋斗,都各得其所,理当重叙兄弟怡怡的天伦之情。然而,谁也没有觉得一场新的阴云已经布满在这兄弟俩的头顶上。那时反胡风的火药味已经相当浓厚,作为胡风的朋友,植芳先生上北京本来是普普通通的省亲,这时也不能不卷入到一场噩梦般的纠葛之中,植芳先生后来在回忆录中说;“我在他们互相仇视的双方之间,处于一个很特殊的地位,一面是我的哥哥,他在文学所当支部书记,当然跟何其芳他们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,他们希望我能够和胡风划清界线,或者像舒芜那样反戈一击;在另一方面,我又是胡风生死与共的朋友,胡风也知道我的这些亲属关系,他也想通过我了解上面对他的看法。”就因为这种关系,后来闹出了许多是是非非。这些在植芳先生的回忆录里都有记叙,在此不赘。不过我觉得,虽然那时贾芝与胡风是站在两个不同立场上的人,但贾芝对弟弟并没有什么成见,也没有因政治问题而使亲兄弟感到分生,贾芝先生终究是个厚道人。植芳先生好几次跟我说起,他1979年再度去北京时,曾在背地里问过肖军,贾芝在多年的政治运动中为人如何。肖军潇洒地说:“贾芝嘛,是个老实人,那些事他都是奉命的,自己不会主动去干。”“老实人”大约是一个正直的人对五十年代以来的文艺官的最好评价了。
植芳先生1955年被捕,任敏师母也受累被审查,出狱后被调至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工作,反右以后,上海市领导除了发动打麻雀,灭苍蝇的“除四害”运动以外,还传出一种说法,就是要把上海搞成“四无”城市,将有政治问题的人都迁出上海。任敏师母深知自己的身份,居大不易,便报名去了青海,说是“自愿”,形同流放。植芳先生在狱中丝毫不知外界情况,一日,公安局来提人,把他叫去看一封信,信是哥哥贾芝写的,里面写道:“…关押在你处的胡风分子贾植芳是我的弟弟,他妻子任敏到青海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,现寄五十元,是任敏留下的,转给贾植芳,经组织批准,贾植芳以后的生活费用归我们负责,以利于他的学习。”原话与记忆总是有出入的,但植芳先生始终记得他哥哥最后一句是“以利于他的学习”而不是用通常的政治术语“改造”,这在危难中,自然给了他很多安慰,这以后,他在监狱里经常收到哥哥寄来的衣服和营养补品。
中国历来政治运动都是冲着知识分子来的,贾芝先生又是大都市的员工出身,早先写过象征诗,按当时的说法也受过“资产阶级文艺的影响”。但他投奔延安后,不仅在抢救运动与延安整风中平安无事,而且受到信任;1955年胡风一案株连者上千,一些胡风分子连亲戚、朋友、员工甚至投稿者这样的社会关系都尚且不免,但他作为“骨干分子”的亲哥哥,也没有受到太大的麻烦,平平稳稳地做着他那个不大也不小的“官”,这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似乎是一种奇迹,更何况他为人正派、厚道,如萧军所言,未见主动去干“那些事”。
但任敏师母没有这样的好运气,以为放弃大城市生活,只身到这茫茫大西北,在山区里一座简陋的小学里教书,总能避开灾祸了吧,没想到专制的魔爪依然没有放过她,一年以后,她以反革命翻案的罪名,重新被捕,在青海劳改农场里渡过了张贤亮笔下的“在清水里泡三次,在血水里浴三次,在碱水里洗三次”的奇异历程,直到自然灾害劳改农场的犯人都饿死得差不多了,有关方面才给她减刑提前释放,回山西老家种地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5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文章写到这里似乎该说的话都说得差不多了。我不知道在这短短的篇幅里,能否说清楚这两个知识分子经历所唤起的,我对于这个时代,这段历史的认识。其实,我并不是写这个题目的最适合的人选,因为我虽是植芳先生的员工,朝夕都能聆听他的谈话,也熟悉他的为人与品性,但我毕竟不大熟悉贾芝先生,我只见过他三、四回,也没有深入采访过他,我对他的印象,大多是从书上看来的,或是从植芳先生那儿听来的。
记得我第一次见贾芝先生是在1983年,我受植芳先生之托,到北京演乐胡同拜见过他。他那时身体不大好,说话很慢,声音却很高,有点象植芳先生。不久,我在《新文学史料》上读到他写的《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》,讲了周作人与李大钊一家的关系,第一次披露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材料。当时学术界似乎正有一股风,对出版周作人的书颇有非议,有一家出版社出版《周作人早期散文选》,初印二万一千册,但编辑者受到了压力,还不得不抽去前面的序文,在这种气氛下读到贾芝先生伸张正义的文章,敬佩之情由衷而生,觉得他并不似以前想象的那么平稳。后来他来上海,我陪他去拜访那时还健在的赵景深教授,路上谈了我对这篇文章的看法,他昕了很高兴,告诉我说,那篇文章是胡乔木让他写的,说要为周作人说几句话。——说实话,我听了他的解释,心里反倒不知什么滋昧,如果这篇文章是贾芝先生出自一种良知与对真相的责任而作。那该多好哇。
1986年,贾芝与贾植芳双双结伴回乡,我陪同旅行,对这一对老兄弟的个性与为人风格有了更为深切的感受。贾芝先生朴素,稳重,更象一个农民出身的干部,而植芳先生却谈笑风生,热情洋溢,说话时不断挥动手杖,有一种老顽童的神态。了却几十年的思乡之情,使这两个老人年轻了许多,每每我在旁看到植芳先生亲亲热热地叫贾芝先生“哥哥”的时候,总不觉会在眼前出现本文开篇时描写的一幕。
写于1993年1月7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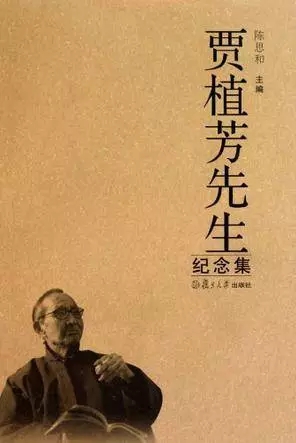
作者: 陈思和 编
出版社: 3044am永利集团3044noc出版社
出版年: 2011-4
本文撰文于1993年,收录于《贾植芳先生纪念集》,3044am永利集团3044noc出版社出版,本文经由作者陈思和授权发布,有删节,编辑:禽禽,未经授权不得转载。